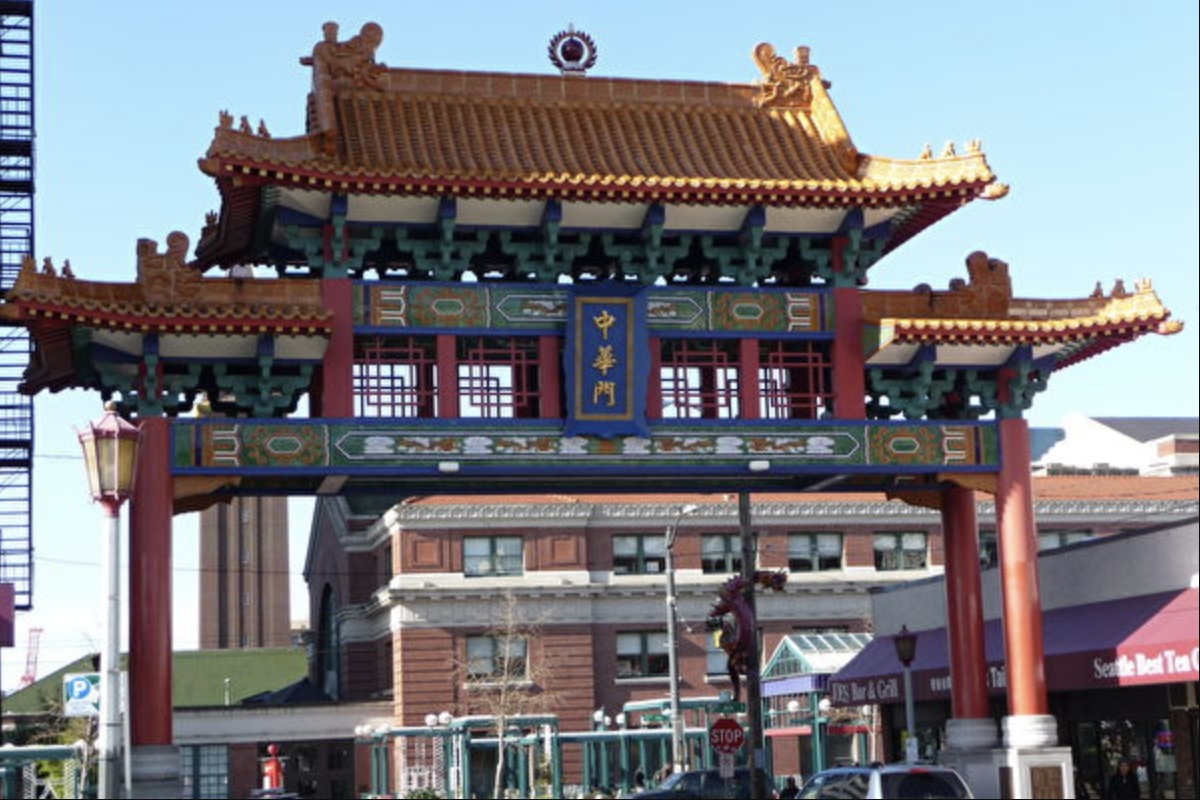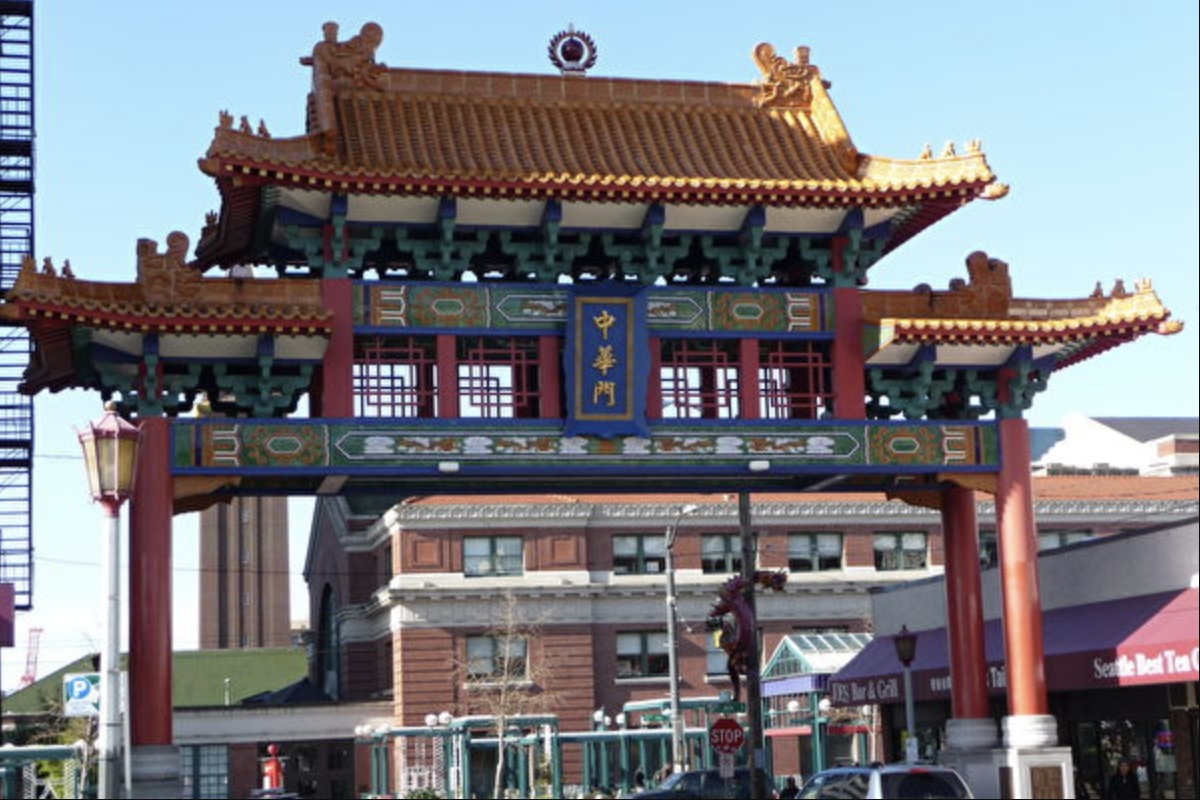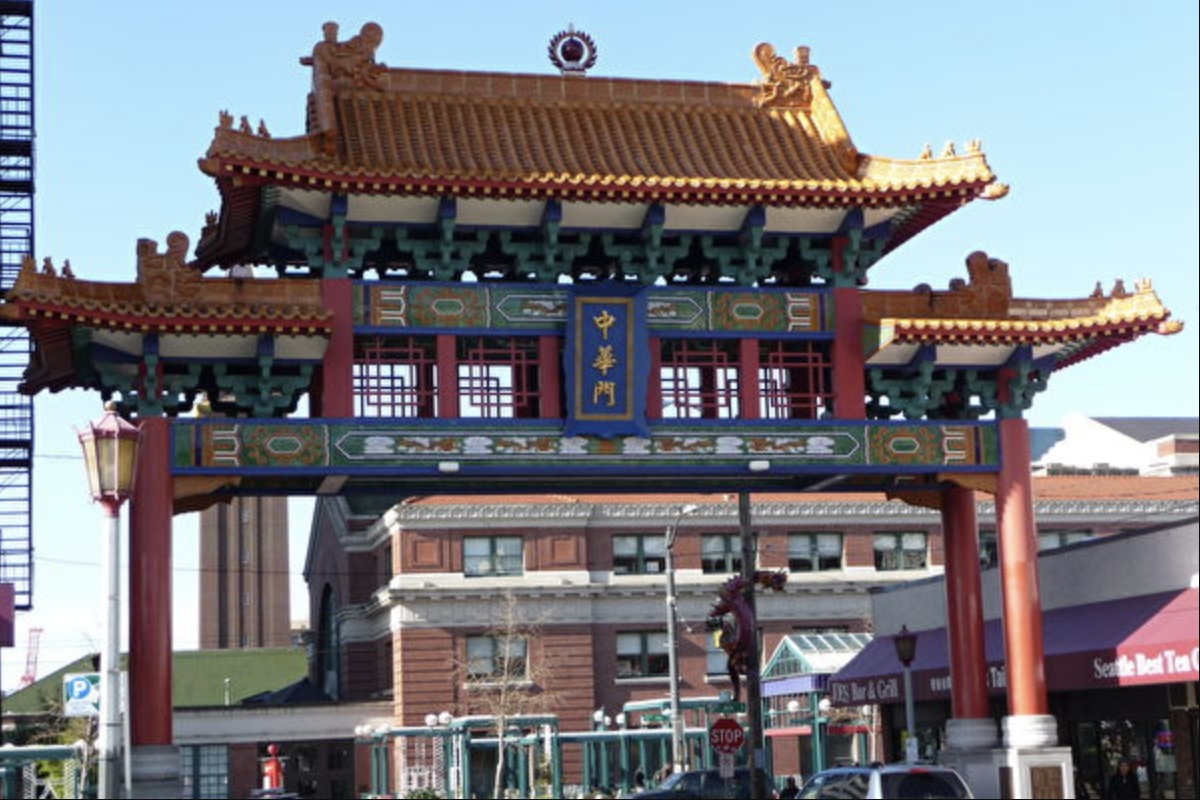
【人民報消息】格蕾絲(Grace)一家目前居住在美國西岸的大城市西雅圖。他們一家的移民始於2009年的一場演講。
格蕾絲:大概是09年吧,呃,在那個墨西哥大使館的演講之後,他講話之後,他就有了朦朧的覺得此地不可留,要至少出去試試、看一看,他就覺得這個風向有點不太對。
移民始於一場演講
【旁白】格蕾絲這段話中提到的第一個他是指習近平,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第二個他是格蕾絲的先生。
記者:你提到墨西哥大使館09年的一個演講,能告訴我是一個什麼樣的演講嗎?
格蕾絲:是一個內部講話,是出訪期間他(習近平)在墨西哥,就是中國駐墨西哥的大使館,他接見使館工作人員和當地的華人華僑代表時的一個講話。那當時以我的這個嗅覺,我並沒有覺得有太大的問題,但是我先生他就覺得有一句話讓他非常非常的彆扭,大概的意思就是說中國的事情中國自己來處理的吧,不需要你們這個外面的人來指手畫腳,我們一沒有輸出革命,二沒有輸出什麼什麼......我當時是覺得,It makes sense(這種說法是合理的)。我先生很有意思,他就說這不就跟家暴打老婆是一個概念嘛,就是說我家暴,這是我自己家裡的事情,你們不許說三道四。
記者:你有沒有問過他,他為什麼對這個說法那麼敏感?當時?
格蕾絲:我有問過他,而且以他的家庭背景來說,我個人覺得他應該是又紅又專的那一類。所以就是我老開玩笑說他,你是天生反骨。他說有可能吧。我試圖問過他,他也試圖想找到答案,但是他找不到答案,他就說,就是我的本能告訴我,這句話說的有問題。
【旁白】格蕾絲和她的先生都是七零後,她的先生畢業於中國最頂尖的大學之一,畢業後又在頂尖的跨國公司工作;格蕾絲也畢業於一流大學,在北京的政府機關作公務員。
記者:他聽到這句話之後,以及後來一系列的形勢發展,他是怎麼理解這樣一個形勢的?我想瞭解的是,就是說這種理解是怎麼導致你們後面要決定移民的。
格蕾絲:呃呃,怎麼講呢?從09年起是一個非常依稀的印象,然後這不就是到了2012年,對吧?當時實際上國內還是有挺高的一個期望的,因為他(習近平)當時說的一些什麼八項規定之類的,你會覺得他非常的親民啊,他很想去打破一些原來老百姓很反感的東西。那麼到了13年吧,十八屆三中全會好像是13年,就是在那個裡面,他說了很多,比如說市場啊,競爭啊,就是你當時聽他說的這一些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事實上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你發現他做的事情和他說的事情實際上相去甚遠,這個本身就造成了一種信任的危機,然後就是一種懷疑,然後這種懷疑慢慢就變成了一種信任的危機。
鮮花似錦、烈火烹油,但不對勁
【旁白】格蕾絲在感覺到對最高領導人的信任危機的同時,本身就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她也體會到國家權力集中所帶來的擠壓。
格蕾絲: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能感覺到,就是控制慾越來越強,權力越來越集中,集中於國家機器。那麼到後面就集中於某一個人,對吧?那這種控制體現在方方面面,體現在經濟上,體現在政治上,體現在社會上。那總體來說我感覺這個社會,就是整個國家是在轉向的,這點我和我先生都有非常明確的感覺。
【旁白】與此同時,格蕾絲感覺到各種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格蕾絲:當時國內確實有很多我們覺得很糟糕的事情。從環境來說,那個時候是污染最嚴重的。從身體健康來說,讓人非常非常的煩躁。我記得好像是從11年在微博上,最早是美國駐華大使館開始發PM2.5,那個時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後孩子也比較小,就很鬧心。
記者:那當時你們對形勢的這種分析和判斷,主要是在你們兩個人之間,還是說你們周圍有一些人,有相似的這種感覺?
格蕾絲:呃,主要是我和他之間,我也有少數的朋友會跟我持相似的這種懷疑,或者對前景開始就是出現比較悲觀了,因為在2012年之前,那個中國,尤其是08年奧運會之後,我們感覺就是鮮花似錦、烈火烹油的感覺,就是已經到了極盛的狀態。但那時候我就開始隱隱約約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旁白】格蕾絲說她感覺到的這種不太對勁是因為她越來越關注公共問題。
格蕾絲:那個時候怎麼講,一些社交媒體的言論箝制還不像現在這麼嚴厲。所以那個時候你還是可以在一些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所謂反賊的言論,或者是持不同政見者,沒有那麼激烈啦,就是他會對社會提出一些批判,會有一些意見領袖他們的某一條帖子可能就會突然讓我有一種靈光乍現的感覺,就是會觸及到這個問題,我原來從來沒有考慮過。對呀,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出了什麼問題呢?
記者:那個時候您的工作狀態是什麼?就是說您開始關注這些公共問題了,是因為和你的工作相關嗎?
格蕾絲:我自己的職業生涯當中,可以說是絕大部分的時間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大勢,包括我所在的這個單位是長期從事高度介入這個對外開放的工作,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密切相關的。所以我已經非常習慣於一種定性的思維,就是我們一定會越來越開放的,我們一定會越來越自由的。但是我就突然發現,從大環境到小環境慢慢地發現有一些變化在悄然的發生,然後讓我開始質疑。
我去過六十個國家
記者:方便說你當時是做什麼工作嗎?
格蕾絲:因為我是一個所謂的外語幹部,就是英語幹部吧。我是講英語的,所以我當時因為我的工作原因,去過差不多六十個國家。
記者:你講到13、14年的時候,你們判斷形勢已經不對了,然後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那個時候就想到要出來了,是吧?
格蕾絲:已經有了這個非常朦朧的想法。那麼對於我來說,應該是熱情並不是那麼高漲,因為坦率的說,以我和我先生各自的工作家庭背景,我們在北京算不上人上人,但至少也是過得非常舒適的。即便是從他的角度而言,如果不是當時因為他的僱主給了他這樣一個非常容易的機會,我們也不會說特別費勁的去辦什麼投資移民,我們是一個比較順水推舟的這樣一個狀態,就很鬆弛,就有這個機會,我就試一試。
【旁白】格蕾絲的先生由於公司的協助,很快辦好了移民手續,並在2016年先行到了美國;直到三年後,格蕾絲和孩子才從北京移民到西雅圖。
記者:在你們移民決定的過程當中,你和你先生之間也沒有多少差異,是嗎?
格蕾絲:差異是有的。嗯,反對談不上,但是是反覆的糾結。因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因為我不覺得我的專業技能在美國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和我過往工作在各方面都比較匹配的一個新的工作。所以你如果從一般世俗的角度來說,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有一個身份地位的下降。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原來的單位裡其實又曾經給過我一次機會,一般人看會是覺得很好的機會,就使得我更加的糾結。所以那個時候我跟我先生經常就是跨時區,要跨著這個將近一萬公里,也就是反反覆覆,就是我的情緒會反覆的波動啊,今天打完四十分鐘的電話,我覺得我已經說服了我自己,我已經找到了我的peace of mind(心靈的平和)。過兩天那個感覺就又回來了,所以那段時間反反覆覆,反反覆覆是有的。最後我還是選擇來。
記者:那你當時決定出來的時候,你到底犧牲了什麼呢?就是你是怎麼克服你的情緒的?
格蕾絲:我怎麼說服我自己的,對嗎?呃,我覺得第一點呢,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從我個人的職業來說,我自己出現了一個職業的瓶頸期,我自己非常非常的迷茫,我不知道接下去我在事業上能做什麼,我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我的專長,我還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壓制我的這種自由的天性啊,去適應這個越來越收緊的大小環境。
為了移民,我犧牲了很多
記者:但是我們知道,就在北京那種地方,如果你是屬於這種比較舒服的位置,是不是意味著你的犧牲其實是很大的?
格蕾絲:嗯,對,就是如果我留在那兒繼續下去,我是可以過得很舒服,然後社會地位感也很強嘛。但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並列第一個原因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家庭吧,就是孩子也慢慢一年一年的在成長,我不可能永遠這樣兩地分居,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家庭吧。所以從孩子的長遠發展來說,考慮到我本人對國內對思想、對言論的這種高度的鉗制和禁錮,我是極其之反感。我對這個可謂用深惡痛絕來形容。所以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思想和言論被高度封閉禁錮的國家裡面長大。
記者:你克服了自己的一些負面的想法,而且對自己的未來的生涯做了一個決斷,然後移民了。然後你們移民的時間是在2019年。2019年移民過來的話,實際上也就是說剛好躲過了疫情,是嗎,可以說你是很幸運的嗎?
格蕾絲:是的,是的,我認為我非常非常的幸運。實際上,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碰巧是在國內的,因為我母親做手術,我就是在2020年一月份的時候回北京了,然後很快的嘛,我記得是1月23號吧,還是25日?
記者:對,是23日。
我為中國人痛哭
格蕾絲:武漢就封城了,對不對?然後不就中美斷航了嘛,我就回不來了,所以我是一直拖到了差不多八月份,2020年的八月份才有飛機可以飛回美國。所以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那個時候鋪天蓋地的那種慘痛啊,武漢發生的事情其實對我是有創傷的。我特別特別清楚的記得李文亮醫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就一個人在房間裡痛哭,就是特別特別的難過。後來我,我就給我先生打電話,他那個時候在美國,就是我電話一接通,我就開始嚎啕大哭,他先是嚇一跳,因為他那時候剛好是在上班路上......直到今天我想起來還是非常非常難過,因為我不知道是在哭他,還是在哭自己,還是在哭所有的中國人,就是很難過。
記者:回首你們整個移民過程,你在美國已經生活了6年,那你覺得你們當初移民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
格蕾絲:是我迄今為止最正確的決定,沒有之一。怎麼講,移民給了我最大可能的自由,我本人對自由的解讀是什麼?就是你永遠會有選擇的餘地,你永遠會有選擇的權利。
記者:你以前有沒有意識到,這種自由、這種選擇對你來講非常重要?
格蕾絲:我以前沒有意識到。以我為例,年輕的時候我就是要閃閃發光,我就是讓每個人都能看得到我,我工作上特別優秀。然後當你實現了這個目標以後呢,你就會發現,OK,我已經得到它了。那下一步呢?那你自然就會去考慮更多的,或者說在我的定義範圍內更高層次的價值,那我定義的更高層次的價值是自由。
記者:所以這裡可以說是你的價值觀的轉變嗎?
格蕾絲:對,可以這麼說。
記者:那麼現在你們的生活當中,談得更多的,或者說,生活的重心是美國嗎?還是中國?那您個人的生活狀態呢?
格蕾絲:我的絕大部分的這個注意力肯定還是放在美國。對國內的這種關注,其實關注一直在,我老開玩笑說是一種叫做閱過即焚,就是我很麻木了,就到了這種情況,就是我覺得Hopeless(毫無希望),就是我不值得再把我的情緒、我的感情再投注在那個方面。我現在既然我們一家人在這裡,我心安處是吾鄉啊!我既然是在這裡,我就應該以這裡為我的家。△(轉自自由亞洲電臺)